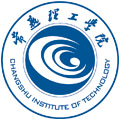西南聯(lián)大的國(guó)民黨籍教授,除少數(shù)在戰(zhàn)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數(shù)是在聯(lián)大時(shí)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過國(guó)民黨,后因長(zhǎng)期不與國(guó)民黨發(fā)生組織關(guān)系,實(shí)已無形脫黨,戰(zhàn)時(shí)又重新填表加入。聯(lián)大教授加入國(guó)民黨的情形比較復(fù)雜,不能對(duì)他們的入黨動(dòng)機(jī)一概而論。
本文摘自《革命與反革命》,王奇生 著,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半數(shù)教授加入了國(guó)民黨這一事實(shí),足以提示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西南聯(lián)大知識(shí)分子與執(zhí)政當(dāng)局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至少意味著,聯(lián)大教授是一個(gè)多元分化的群體,其中既有聞一多那樣的“民主斗士”,亦有姚從吾這樣的“堅(jiān)貞黨員”,更多的可能是介于兩者之間。
西南聯(lián)大的國(guó)民黨籍教授,除少數(shù)在戰(zhàn)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數(shù)是在聯(lián)大時(shí)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過國(guó)民黨,后因長(zhǎng)期不與國(guó)民黨發(fā)生組織關(guān)系,實(shí)已無形脫黨,戰(zhàn)時(shí)又重新填表加入。聯(lián)大教授加入國(guó)民黨的情形比較復(fù)雜,不能對(duì)他們的入黨動(dòng)機(jī)一概而論。
率先加入國(guó)民黨的,是擔(dān)任學(xué)校及院系行政職務(wù)的一批教授。當(dāng)陳立夫、張厲生要求蔣夢(mèng)麟在西南聯(lián)大建立國(guó)民黨直屬區(qū)黨部后,蔣夢(mèng)麟立即擬具計(jì)劃:“第一步先介紹聯(lián)大之各長(zhǎng)之未入黨者入黨;第二步介紹北大清華南開各校原來之各長(zhǎng)入黨;第三步聯(lián)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來之各系主任。如是則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為黨員,則以后推行黨務(wù),如順?biāo)浦垡印?rdquo;《蔣夢(mèng)麟復(fù)陳立夫、張厲生函》(1939年7月15日)。1939年7月23日,蔣夢(mèng)麟召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院處以上教授舉行茶會(huì),宣布“凡在聯(lián)大及三校負(fù)責(zé)人,其未加入國(guó)民黨者,均先行加入”。《清華大學(xué)校史稿》,第296~297頁(yè);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zhǎng)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頁(yè)。會(huì)后不久,馮友蘭等十余位擔(dān)任行政職務(wù)的教授即首先加入。
馮友蘭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過國(guó)民黨,但入黨后對(duì)參加實(shí)際革命活動(dòng)缺乏興趣和熱情,到1926年便自行脫黨。南京政府建立后,馮友蘭沒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馮友蘭訪蘇歸來,因其言論有“宣傳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雖然僅關(guān)押了一天,但在馮氏心中,難免留下?lián)]之不去的陰影。參見翟志成《馮友蘭徹底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1895~1945)》(五),《大陸雜志》(臺(tái)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此次在聯(lián)大重新入黨,據(jù)馮友蘭后來解釋:“蔣夢(mèng)麟約我們五位院長(zhǎng)到他家里談話。他說:‘重慶教育部有命令,大學(xué)院長(zhǎng)以上的人都必須是國(guó)民黨黨員。如果還不是,可以邀請(qǐng)加入。如果你們同意加入,也不需要辦填表手續(xù),過兩天我給你們把黨證送去就是了。’當(dāng)時(shí)只有法學(xué)院院長(zhǎng)陳序經(jīng)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沒有發(fā)言表態(tài)。我回家商量,認(rèn)為我已經(jīng)有過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對(duì)蔣夢(mèng)麟的提議,恐怕重慶說是不合作,只好默認(rèn)了。過了幾天,蔣夢(mèng)麟果然送來了黨證。”馮友蘭著、蔡仲德編《我的學(xué)術(shù)之路——馮友蘭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第111頁(yè)。
馮友蘭的憶述,與實(shí)際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長(zhǎng)陳立夫與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張厲生給蔣夢(mèng)麟的指令,并無“大學(xué)院長(zhǎng)以上的人都必須是國(guó)民黨黨員”之類旨意。蔣夢(mèng)麟要求院處以上負(fù)責(zé)人先行加入,應(yīng)只是勸進(jìn),而非強(qiáng)制。1940年3月,蔣介石聽說教育部命令全國(guó)中小學(xué)教員須一律入黨,十分不滿。他在給教育部長(zhǎng)陳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強(qiáng)迫中小學(xué)教員入黨,其作用與事實(shí)太不相宜。陳立夫呈復(fù)說: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盡量介紹中小學(xué)教職員入黨,但始終未有強(qiáng)迫必須一律入黨之說。見《關(guān)于各校區(qū)黨部之籌設(shè)》,黨史館:特3—261。事實(shí)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負(fù)責(zé)人都加入了國(guó)民黨,如法商學(xué)院院長(zhǎng)陳序經(jīng)等人即拒絕加入。陳序經(jīng)在拒絕入黨后,其職位并未受到影響。另如浙江大學(xué)校長(zhǎng)竺可楨多次拒絕加入國(guó)民黨,竺可楨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擔(dān)任浙江大學(xué)校長(zhǎng)。在任期間,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兩次拒絕加入國(guó)民黨,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團(tuán)第一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時(shí),因被選為三青團(tuán)中央監(jiān)察委員,無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團(tuán);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國(guó)民黨,而此前全國(guó)大學(xué)校長(zhǎng)中,只有他一人為非國(guó)民黨員。見《竺可楨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冊(cè),第234、316頁(yè);第2冊(cè),第673、680、775頁(yè)。亦未影響其職位。
當(dāng)時(shí)的實(shí)際情形是,聯(lián)大各院系負(fù)責(zé)人對(duì)國(guó)民黨的入黨邀請(qǐng),多數(shù)采取了合作而非對(duì)抗的態(tài)度。馮友蘭當(dāng)時(shí)雖然沒有加入國(guó)民黨的積極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學(xué)術(shù)與政治須分途為由,謝絕了朱家驊要他為三青團(tuán)向青年作號(hào)召的請(qǐng)求。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zhǎng)編》,第244頁(yè)。但他并沒有拒絕蔣夢(mèng)麟送來的國(guó)民黨黨證。這種合作而非對(duì)抗的態(tài)度,大體代表了戰(zhàn)時(shí)相當(dāng)一部分知識(shí)分子在“團(tuán)結(jié)御侮”的大背景下對(duì)執(zhí)掌政權(quán)的國(guó)民黨之真實(shí)心態(tài)。參見翟志成《馮友蘭徹底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1895~1945)》(六),《大陸雜志》(臺(tái)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尤其是抗戰(zhàn)初期,多數(shù)知識(shí)界精英將抗戰(zhàn)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國(guó)民黨,加入國(guó)民黨,在某種意義上也表示自己與執(zhí)政當(dāng)局共渡艱難一致對(duì)外的決心。此一論點(diǎn),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兩人論文中均有提及。即使如竺可楨那樣“對(duì)入黨事極不熱心”,并對(duì)國(guó)民黨的一些作為不愿茍同的人,亦表示“對(duì)國(guó)民黨并不反對(duì)”。《竺可楨日記》第2冊(cè),第768頁(yè)。另?yè)?jù)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記載,羅常培給聞一多一份入黨申請(qǐng)書,拉聞入黨。聞?dòng)行﹦?dòng)心,邀朱自清一同參加。朱以“未受到邀請(qǐng)”為由婉拒。受朱的影響,聞才打消了入黨的念頭。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頁(yè)。據(jù)此觀之,后來以“民主斗士”著稱的聞一多,直到此時(shí),對(duì)國(guó)民黨尚無明顯敵對(duì)情緒。若非朱自清勸阻,聞也許就加入了國(guó)民黨。
除院系負(fù)責(zé)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yàn)樗饺饲檎x,或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地成為國(guó)民黨體制中的一員。1939年11月,朱家驊接替CC系干將張厲生擔(dān)任國(guó)民黨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在此之前,蔣介石一直將黨務(wù)交付給二陳(果夫、立夫)為首的CC系掌控。CC系對(duì)黨務(wù)資源的長(zhǎng)期壟斷,導(dǎo)致不少人因厭惡其派閥作風(fēng)而不愿加入國(guó)民黨。甚至有些行政部門為了防御CC系勢(shì)力的滲入而抵制設(shè)立國(guó)民黨黨部。參見拙著《黨員、黨權(quán)與黨爭(zhēng):1924~1949年中國(guó)國(guó)民黨的組織形態(tài)》,第320~321頁(yè)。與陳立夫、張厲生等純粹的“黨官”有所不同,朱家驊可以稱得上是一個(gè)政學(xué)兩棲人物。留學(xué)德國(guó)的學(xué)歷背景,北京大學(xué)教授、中山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中央大學(xué)校長(zhǎng)等任職經(jīng)歷,以及中英庚款董事會(huì)董事長(zhǎng)、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等顯赫頭銜及其所掌控的豐富的學(xué)術(shù)資源,使朱家驊在知識(shí)界具有深厚的人脈基礎(chǔ)。朱在知識(shí)界不僅朋友眾多,而且相當(dāng)一批人對(duì)他執(zhí)弟子禮。正是與學(xué)界人物之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朱家驊在出任國(guó)民黨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后,有意要將黨務(wù)推進(jìn)校園。在其直接籠絡(luò)或間接影響下,相當(dāng)一批知識(shí)精英相繼加入國(guó)民黨。在此之前,很多知識(shí)界人士對(duì)CC系控制的國(guó)民黨敬而遠(yuǎn)之。而朱家驊接掌國(guó)民黨組織大權(quán)后,很快成為執(zhí)政黨聯(lián)絡(luò)和親近知識(shí)界的一個(gè)重要橋梁。
姚從吾原本是一個(gè)埋首書齋的純粹學(xué)者,自稱“與外間斷絕往還,專心治史”,“一向不談?wù)危c任何組織不生關(guān)系”。《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39年7月16日)。當(dāng)朱家驊推薦其擔(dān)任聯(lián)大三青團(tuán)負(fù)責(zé)人時(shí),他列舉多種理由表示“懇辭”。后得知此事已由蔣介石批準(zhǔn)發(fā)表,并出于對(duì)朱家驊這位師長(zhǎng)的尊重,姚勉為其難地接受了。朱家驊轉(zhuǎn)任國(guó)民黨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后,姚也隨之擔(dān)任聯(lián)大區(qū)黨部書記。在此期間,姚逐漸對(duì)政治產(chǎn)生了“不感興趣”的興趣,并由一名“純粹的”學(xué)者逐漸轉(zhuǎn)化為一名忠貞的國(guó)民黨黨員。姚擔(dān)任聯(lián)大區(qū)黨部書記期間,又介紹身邊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繼加入了國(guó)民黨。羅常培、賀麟、雷海宗、華羅庚等人均是在姚從吾的動(dòng)員和慫恿下,通過朱家驊親自介紹加入的。姚向朱家驊坦承,在西南聯(lián)大國(guó)民黨組織發(fā)展過程中,私人情誼遠(yuǎn)勝過組織關(guān)系。當(dāng)他向朱家驊推薦某教授入黨時(shí),除簡(jiǎn)介其學(xué)問品行外,還會(huì)介紹該人的私誼關(guān)系。姚從吾推薦給朱家驊的人,大多與朱家驊有一定的學(xué)緣關(guān)系,或留學(xué)德國(guó),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國(guó)知識(shí)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學(xué)背景,常常是影響他們相互聚合或疏離的重要因素。顯然因?yàn)橹旒因懙年P(guān)系,西南聯(lián)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紹加入了國(guó)民黨。姚從吾在致朱家驊的信中這樣寫道:“凡與先生有學(xué)誼者,第一虛心請(qǐng)其與黨合作,其次當(dāng)使為黨之諍友,再其次亦為黨部之朋友。”《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42年6月3日)。被介紹者中,有的對(duì)入黨比較積極,有的雖不大情愿,但礙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絕而勉強(qiáng)加入。如史學(xué)系主任雷海宗,與姚相交甚密。姚對(duì)其反復(fù)游說,雷仍有些猶疑。姚請(qǐng)朱家驊親自出面邀雷入黨,雷礙于情面方表示允可。《姚從吾、王信忠致朱家驊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該函原件無時(shí)間,年月系根據(jù)信的內(nèi)容推斷);《朱家驊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復(fù)朱家驊函》(1942年12月31日)。
聯(lián)大三常委之一的張伯苓是1941年加入國(guó)民黨的。最初孔祥熙曾讓行政院參事張平群動(dòng)員張伯苓入黨。繼而貴州省政府秘書長(zhǎng)鄭道儒亦向張作過同樣請(qǐng)求。最后是國(guó)民黨秘書長(zhǎng)吳鐵城親赴張氏寓所,請(qǐng)其參加,并將黨證放置在張伯苓的桌上。張伯苓礙于情面,不好意思將黨證“璧還”,只好認(rèn)可。參見《南開大學(xué)校史》,第271頁(yè)。
聯(lián)大教授中,考量個(gè)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其人。其實(shí)黨票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機(jī)會(huì),多是希望通過入黨而與朱家驊建立私人關(guān)系。姚從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評(píng)聯(lián)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祿,“利害觀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驊說:聯(lián)大教授“大抵學(xué)有專長(zhǎng),各有獨(dú)見,均愿與政府及黨國(guó)中樞要人私人發(fā)生關(guān)系,以言黨務(wù),則均事規(guī)避,故黨務(wù)工作推行實(shí)難”。《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42年2月10日)。之所以如此,與國(guó)民黨的組織體制大有關(guān)系。國(guó)民黨雖然號(hào)稱“以黨治國(guó)”,但在人事任用和晉升時(shí),黨籍有無,實(shí)無關(guān)宏旨。對(duì)謀職謀位者而言,關(guān)鍵是有無奧援,有無私人背景。
戰(zhàn)時(shí)國(guó)民黨發(fā)展黨員,有幾種不同途徑:一是通過基層區(qū)分部介紹、吸收,這是正途;二是集體入黨,軍隊(duì)士兵入黨大多采取這一方式;三是由國(guó)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與各省市黨部直接征求,特許入黨,這種方式主要面向知識(shí)精英和各界名流。參見拙著《黨員、黨權(quán)與黨爭(zhēng):1924~1949年中國(guó)國(guó)民黨的組織形態(tài)》,第300~302頁(yè)。通過朱家驊介紹特許入黨,一則可以體現(xiàn)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則可以借機(jī)與介紹人建立私人交情。聯(lián)大教授中那些想與“黨國(guó)中樞要人”發(fā)生私人關(guān)系者,亦希望借由朱家驊介紹入黨而與朱建立私誼,對(duì)國(guó)民黨的“公”組織并無多大興趣。
為了迎合這種心理,姚從吾在介紹教授入黨時(shí),經(jīng)常轉(zhuǎn)請(qǐng)朱家驊親自寫信邀請(qǐng);每當(dāng)有黨員教授赴重慶時(shí),姚會(huì)函請(qǐng)朱家驊親自接見他們,以示籠絡(luò)。此種情形不止在聯(lián)大,在其他大學(xué)也同樣存在。如中山大學(xué)區(qū)黨部書記任國(guó)榮在給朱家驊的信中寫道:“區(qū)黨部之執(zhí)行委員會(huì)已無形解散,本可從新選舉,但一般心理,皆極愿與鈞長(zhǎng)發(fā)生直接關(guān)系。故鄙見以為不如仍由中央選派。”《任國(guó)榮致朱家驊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驊檔·學(xué)校黨務(wù)卷》:95-(5)。任國(guó)榮所稱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學(xué)區(qū)黨部委員不愿自下而上地由黨員選舉產(chǎn)生,而極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選派。所謂“中央選派”者,實(shí)際上由朱家驊選派。被選派者即多因此而與朱氏個(gè)人結(jié)緣,或進(jìn)而成為“朱派”中的一員。朱家驊本人顯然也樂意利用此種“一般心理”,以網(wǎng)羅人馬,壯大自己的派系勢(shì)力。就派系屬性論,朱家驊原本與CC系較為親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后,開始自組班底,另樹一幟。由于朱家驊在學(xué)界政界均有相當(dāng)?shù)牡匚慌c歷史基礎(chǔ),自立門戶后,很快成長(zhǎng)為戰(zhàn)時(shí)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漸與CC系形成分庭抗禮之勢(shì)。據(jù)長(zhǎng)期擔(dān)任國(guó)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huì)秘書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huì)秘書長(zhǎng)的王子壯觀察,戰(zhàn)時(shí)朱家驊系與CC系在地方層級(jí)的沖突相當(dāng)激烈。“蔣先生對(duì)于其干部,似采牽制政策,果夫立夫組黨十年而有所組織,自然在黨中形成一個(gè)力量,朱騮先(家驊)來長(zhǎng)組織,因其在學(xué)界政界均有相當(dāng)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舊軌,于是下級(jí)沖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陜西、山東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頓,更談不上下級(jí)之健全。”見《王子壯日記》第9冊(cè),臺(tái)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33頁(yè)。
聯(lián)大教授中,還有一批主動(dòng)申請(qǐng)加入者。在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張文裕(物理)、孟昭英(無線電)、范緒筠(無線電)、趙九章(氣象)、蘇國(guó)楨(化工)、王德榮(航空工程)、閔嗣鶴(數(shù)學(xué))、施惠同(數(shù)學(xué))、葉楷(電機(jī)工程)、馬大猷(電機(jī)工程)、李慶海(土木工程)、葉日葵、鄭師拙等。他們之入黨,多是華羅庚引介的。
據(jù)華羅庚自述,他在北伐時(shí)期(1926年)加入過國(guó)民黨。北伐后,他因沒有參加登記而自動(dòng)脫黨。1942年12月,華由朱家驊介紹重新入黨。《華羅庚致朱家驊函》(1942年12月19日):“騮先部長(zhǎng)先生賜鑒:遙頒大教,語重心長(zhǎng),謀國(guó)之忠,垂念之切,躍然紙上。羅庚敢不奉教,今后當(dāng)體念國(guó)父遺教、總裁訓(xùn)誨,以追隨先生為黨為國(guó),盡其綿薄。溯民十五時(shí),羅庚曾在滬入黨。其時(shí)軍閥之勢(shì)猶張,革命之花未發(fā),北伐成功后,羅庚為經(jīng)濟(jì)所困,不得不負(fù)責(zé)經(jīng)營(yíng)先父之店鋪,日則持稱運(yùn)籌,晚則研習(xí)算學(xué),每日工作有過于十六小時(shí)者,致對(duì)黨務(wù)方面因循未暇登記。今常戚戚,愧為國(guó)父信徒。今先生振聵啟蒙,使羅庚得生新機(jī)而還舊識(shí),感激之殷,有若撥云霓而見天日者……”《朱家驊檔·人才人事卷》:459—(2)。華羅庚入黨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黨。華羅庚將他們一一引薦給朱家驊。《華羅庚致朱家驊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驊檔·人才人事卷》:459—(2)。華羅庚還致函朱家驊,主動(dòng)請(qǐng)求赴重慶中央訓(xùn)練團(tuán)受訓(xùn)。當(dāng)時(shí)國(guó)民黨中央有規(guī)定,凡戰(zhàn)時(shí)出國(guó)人員,都必須先到中央訓(xùn)練團(tuán)受訓(xùn)。朱家驊考慮到華羅庚身有殘疾,從昆明赴重慶,路途遙遠(yuǎn),行動(dòng)不便,勸他不要受訓(xùn),并允諾華羅庚,“茍他日有機(jī)會(huì)出國(guó),可代其證明”。華羅庚回復(fù)說:“羅庚請(qǐng)訓(xùn)之鄙意,實(shí)為慕風(fēng)而非徒為出洋計(jì)也。溯羅庚自民十四折節(jié)讀書以來,久違黨教,凡百舉措,類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黨以后,每思有以報(bào)黨之道,但常有不知從何處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茍能來渝聆訓(xùn),飽識(shí)時(shí)宜,或可為黨盡一分力量,而不致徒為掛名黨員而已也。”《華羅庚致朱家驊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驊檔·人才人事卷》:459—(2)。朱家驊感其意態(tài)殷懇,由中央組織部寄去旅費(fèi)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華羅庚入中央訓(xùn)練團(tuán)受訓(xùn)。受訓(xùn)期間,他還專門就黨團(tuán)問題與黨國(guó)要政,向朱家驊進(jìn)言獻(xiàn)策。據(jù)姚從吾稱,華在入黨之前,曾上書蔣介石,“條陳青年問題,頗蒙獎(jiǎng)許”。《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42年11月28日)。1945年5月,國(guó)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大會(huì)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時(shí),朱家驊簽呈總裁蔣介石,將華羅庚列為中央委員候選人。華羅庚雖然最終未能當(dāng)選,但對(duì)朱家驊“感深銘腑,莫可言宣”。《華羅庚致朱家驊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驊檔·人才人事卷》:459—(2)。
華羅庚的情形在聯(lián)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們并非完全沉潛書齋,不問政事。至少在抗戰(zhàn)時(shí)期,他們中不少人對(duì)國(guó)民黨實(shí)際抱有相當(dāng)?shù)耐楹椭С帧?/p>
1945年國(guó)民黨六大召開前夕,朱家驊與陳立夫聯(lián)名向蔣介石推薦了98名“最優(yōu)秀教授黨員”,內(nèi)有:黎錦熙(西北師范學(xué)院),陳寅恪(燕京大學(xué)),伍蠡甫(復(fù)旦大學(xué)),熊慶來(云南大學(xué)),薩本棟(廈門大學(xué)),金毓黻(東北大學(xué)),竺可楨(浙江大學(xué)),王星拱、朱光潛(均武漢大學(xué)),張伯苓、蔣夢(mèng)麟、梅貽琦、馮友蘭、賀麟、華羅庚、姚從吾(均西南聯(lián)大)等。王奇生
中國(guó)-博士人才網(wǎng)發(fā)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wǎng)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wǎng)轉(zhuǎn)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chǎn)業(yè)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diǎn)或證實(shí)其內(nèi)容的真實(shí)性,文章內(nèi)容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