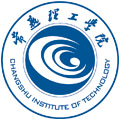一個情侶伙伴知道如何激勵、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點子。

圖片來源:Thinkstock
物理學家Claudia Felser和Stuart Parkin相識于一次應用電磁學會議上,他們立刻被對方吸引。但是他們之間的交談可謂三句話不離本行。
Parkin對發現能用于制作微型數據存儲設備的材料十分感興趣。Felser則更偏愛赫斯勒化合物的話題,這種合金具有可改變的磁特性。“但是他不感興趣。”她笑道。Parkin認為這種化合物聽上去可能難以與其他材料相連接。“所以這不是一次成功的會面。”Felser說。
但是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系。當Felser分享了她對赫斯勒化合物的半導體和量子特性日益增長的知識后,Parkin開始對這種分子越來越好奇。2009年底,她決定利用休假時間從德國前往IBM總部工作,Parkin正就職于這里。“我要請她與我在一起。”Parkin說。從此他們走在了一起。“我們現在仍然在一起工作。”他說。
Felser和Parkin是成千上萬通過科學相遇的夫婦中的一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0年調查顯示,具有博士學位的已婚人士中,超過1/4的人的伴侶也供職于科學或工程學領域。這一數字在增長:1993年,該比例為1/5。越來越多的機構在雇傭夫妻。2008年,一項涉及9000名美國研究人員的調查發現,夫妻比例從1970年的3%上升到21世紀的13%。在線約會服務PlentyOfFish的數據揭示,與平均用戶相比,擁有研究生學位的用戶與具有同等學歷的人結為伴侶的幾率高3倍。合作是科學研究的關鍵,當合作雙方是伴侶時,這種關系能提供一些獨一無二的優勢——更了解彼此的個性和動機,當然這項工作也有占據晚餐話題的風險。
材料和里程
Felser休假結束返回德國后,她和Parkin開始積累航空里程。而且Parkin的務實態度感染了“作為一個化學家,你想去理解黏合,希望找到新的合成方法,但不會深入思考應用。”她說。現在,她也開始考慮材料的成本和穩定性。“你真的要學會各種思考。”Felser說。2011年,這對夫婦發表了有關赫斯勒化合物的論文。
在過去幾年里,Felser和Parkin想盡一切辦法聚在一起。學術會議成為他們見面的有效方式。“一旦人們注意到我們是伴侶,他們便開始邀請我們共同參加一些會議。這很好。”Felser說。
Felser的老板(現為馬普學會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甚至認為她們或許可以說服Parkin接受一個德國職位。經過數年奔波于不同大陸之后,Parkin最終出任馬普學會微觀結構物理學所所長。4月,他獲得芬蘭技術學會千年技術獎,并計劃把獎金的一部分用于在河邊建一座房子。他們計劃于12月結婚。“漢莎航空和聯合航空將會不開心。”Parkin說。
神經元連接
Lily和Yuh-Nung Jan致力于研究細胞分裂,但他們自己卻不能分離。他們開始談話的第一個詞總是“我們”或“我們的”。甚至他們的實驗室也連在一起。他們相識于1967年的中國臺灣,那時他們都在攻讀物理學。
Yuh-Nung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他和同學在山區進行慶祝旅行。與他們一起的是一個來自低年級的學生:Lily。她跳了一級,趕上了Yuh-Nung,并且也申請讀研。他們都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物理學,但頭3年他們住在各自的宿舍。不久之后,一個契機讓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職業選擇。“回到臺灣他們將無法接觸現代生物學。”Yuh-Nung說。
之后,他們轉入細胞生物學領域,并且開始合作。1971年,他們結婚。1979年,他們來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這里,他們在同一實驗室的類似項目上度過了數年時間。于是,他們自然而然地聯合運行了一間實驗室。
有點像太多廚師燒出難喝的肉湯。“最初,我們都帶著博士后或學生,并且工作難以繼續,因為兩個人難有相同的觀點。”Lily說,“很快演變成爭論。”他們現在運行著相鄰的實驗室,指導著29位研究人員,并堅持在頂級刊物發表文章。Lily側重離子通道,而Yuh-Nung致力于細胞形態學研究。
“這不光是1+1,而且要好得多。”Lily說,“無論你想起什么,都能在家或在工作中相互討論。”Yuh-Nung也說,“我們在一起超過40年,她是我的伴侶,我感到非常幸運。”
家系圖
很少能有研究者聲稱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科學領域——更不用說是與配偶一起了。但是進化生物學家Mark Pagel和人類學家Ruth Mace恰好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是在人類學中使用種系發生(進化樹)的先驅。
他們的第一次碰面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英國牛津大學動物學部,但他們的工作完全沒有重合。Mace專攻動物生物學,而Pagel致力于開發物種關聯性分析方法。而這些都深受他們所學的進化生物學影響。
英國進化學家因為用適應能力和自然選擇來解釋行為的觀點而聞名。“我們都離開了這個‘教會’。”Mace說。他們第一次見面是這個部門的上午休息時間,這給了他們充足時間討論各自的觀點。
幾年之后,Pagel和Mace合作了一篇論文,使用系統發生方法分析人類文明,并認為正如動物學家使用遺傳學研究物種進化那樣,人類學家也應該用語言研究人類文明進化。同一年,他們的長子出生,為他們自己的生命樹增添了一個小小的枝椏。
盡管他們仍然合作文章和研究項目——Mace預計他們有大約10%的工作在一起,但他們仍保持獨立的研究身份。他們也都有種系發生學之外的學術興趣。另外,重疊領域的工作也會引發一些尷尬情況,尤其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的姓氏。有時,一個人會被要求評議另一個人的論文或競爭性經費申請,通常他們會以利益沖突的借口來拒絕。
夢之隊
有時,在海洋生態學畢業作品中,Boris Worm可能是在睡眠中解答問題。醒來以后,他會將自己的夢境告訴伴侶Heike Lotze。作為海洋生態學者,Lotze充當起了沉睡共鳴板。“早上你會忘記夢境。但是如果旁邊有人,你可以馬上告訴他們。”Worm說。
這兩位生態學家相信,他們的關系有助于形成其早期研究,而如果不是情侶關系將很難做到這一點。Worm 提到:“我們能在一開始分享點子,也許它們非常粗糙、沒有完成,而且沒有用處,但十分有趣。”Lotze也說:“我常常有創造性、憑借直覺獲得的想法。我覺得應該把這些粗糙的東西交給Boris,然后由他來塑造。”
Worm和Lotze相識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他們在德國攻讀研究生。他們的研究領域重疊,但追求的卻是不同方向。Lotze傾向于人類對海洋的影響,研究方向為營養物污染——這被認為是藻華的成因。Worm則更偏重于分析,也更加理論化。作為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的兒子,他對人際關系和社團考慮良多。“Heike的視角接觸到我的觀點,然后為它們裝上輪子,或許我能為她提出的問題提供一些更寬泛的背景。”他說。
整個博士期間,他們工作在一起,甚至在相同的地方學習。由于他們的實驗通常密切相關,所以在出版前不得不做一些分解工作。“我們會坐下來,然后說,我將發表這個,另一些是你要發表的。”Lotze說。2002年,他們聯合發表了第一篇大論文,并常常共同發表文章。
而且,Worm通常是他們觀點的第一發言人。“我在后面多一點,人們通常更多見到Boris。”Lotze說。但她最終決定走到前臺,“我不想躲在影子里。我也需要戰斗”。
去年,這對夫妻贏得了首個共同榮譽——彼得·本奇海洋科學卓越獎。“這樣的關系不常得到正式認可,這種感覺很美妙。”Worm說。但對他們來說,合作的最大意義是無形的。一個情侶伙伴知道如何激勵、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點子。正如Lotze 所說的:“你的伙伴是最好的批評者。”(張章)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業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文章內容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