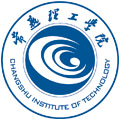這些出自各學科間非正常“聯姻”的成果,不太可能產生自典型的大學。
圖片來源:Andy DeLisle/ASU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ASU)有一間巨大的玻璃墻房間,里面的世界既熟悉又陌生。月球表面圖片出現在巨大的熒幕上,行星學家Jim Bell正在炫耀該校一架安裝在月球探測器上的攝影機拍攝的全景圖像。Bell還興致勃勃地提到,計劃造訪一個奇怪的地方:幾乎全部由鐵構成的名為賽克的 小行星。研究人員一直熱切地希望能探索那里,因為它基本是地球金屬核的裸體版本,擁有科學家從未見過的東西。
但是,研究這顆距離地球2.55億公里的快速旋轉的金屬小行星需要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密切合作。Bell發(fā)現,在ASU,這樣的合作比他在康奈爾大學時更加容易。
“(在 康奈爾大學)工程師在校園的另一端工作,因此當你想出一個有關儀器的點子后,‘扔’給他們,差不多1年以后,他們才將設計‘丟’還給你,而且可能未必有 用。”他說。但在ASU,Bell供職于地球和空間探索學院(SESE),這里既有工程師也有計算機學家。“對相同學科感興趣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們能更快 更好地做事情。”
喜憂參半
SESE 成立于2006年,前身為天文和地質學系,它是Michael Crow雄心壯志的具體體現。Crow在2002年出任ASU校長,他希望能將這所中等公立大學打造得更好。Crow試圖通過拆掉傳統(tǒng)學院之間的“墻壁” 和將不同學科結合起來組成更大的集合,從而轉化ASU的研究和教育。“我們應該通過讓他們處理當代的重大議題,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學生和世界。”他說。
在他超過10年的任期中,結果可謂喜憂參半。值得肯定的是,ASU吸引了超過兩倍的研究經費。大學文化開始轉入開展跨學科研究和教育。“亞利桑那做的一些事情將有實際影響。”斯坦福大學多學科研究所Bio X物理學家Daniel Fisher說。
但就另一個角度而言,ASU的變化只是微小的改變,例如,在傳統(tǒng)部門之上分層新研究機構。而且,改造的努力可能不會從根本上提升ASU的科研水平。《自然》雜志進行的一項學術產出分析顯示,一些措施提升了ASU的數據,例如論文出版數量,但與類似研究機構相比,該校的進展甚微。
不過,這些結果提示,對于雇傭了數千研究者的大學而言,通過根除學科間的溝壑改變其本質特性有多么困難。即使Crow強調:“我們遇到的最大挑戰(zhàn)是‘無形’學院的力量,實際上,人們對自己的學科存有更大的忠誠。”
推倒壁壘
改革的信號仍然遍及這所大學。門廊的巨幅海報宣告“一所新的美國大學”伴隨有8個野心勃勃的行動呼吁。“融合知識學科”“改革社團”“重視企業(yè)家精神”“讓學生成功”和“進行靈感研究”等。校園本身也具有現代功利性的外觀:巨大的流線型建筑,頂部裝有太陽能板。
這 里的注冊學生(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在美國首屈一指,約有7.6萬人。同時,該校也聘請了許多新職員,ASU的1700位終身職位教員中近500位受雇于 過去10年,該校著重挑選那些能與他人協作工作和超越學科界限的職員。“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如果房間開門了,大家都要為爭奪實驗室地盤‘激戰(zhàn)’。”ASU 生物設計學院微生物學家Cheryl Nickerson說。Nickerson為美國宇航局空間任務提供細菌,與許多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共事,他說:“而在這里,我不說我們是完美的,但很多時 候我看到人們把空間讓給有擴展項目的同事。”
所 有這些改變都是Crow改造這所大學的宏偉計劃的一部分,同時,他在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主持或參與了若干國家委員會,包括該國商務部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 家精神咨詢委員會。在公開演講中,Crow提到最多的就是ASU如何將狹窄的學術院系變?yōu)榇笮偷木C合學術部門。“很多校長都支持跨學科的理念,但Crow 走得最遠、聲音最大。”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家Jerry Jacobs說。
生 物設計學院Joshua LaBaer 提到,Crow的方式是直接和侵略性的。但LaBaer也認為,Crow和團隊的決策通常是合理的。“我沒遇到過教職員對此產生抱怨。”他說,“這里的目 標是好的,你可以利用一些新機會。”2013年,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為ASU研究人員提供了4800萬美元經費,其中約2200萬美元劃撥給生物設 計學院,相比之下,該校在2003年僅從NIH獲得2000萬美元資金。
這 些資源幫助LaBaer建造了用于生產和分析成千上萬蛋白質的獨一無二的設備,以便研究蛋白質的機能及其在疾病中的角色。在裝滿自動化設備的實驗室里,人 類細胞培養(yǎng)液攪動著試管里的蛋白質,然后機器臂將這些分子攬入機器,確定它們的序列和結構。科學家之后會將蛋白質進行對比,以確定哪些形狀和折疊與特定疾 病有關。
ASU的一個優(yōu)先事項正是推動此類生物醫(yī)學研究,并且它已經與附近的梅約診所加強合作。這些合作幫助ASU將LaBaer從哈佛大學吸引到自己旗下。
在 Crow和同事開始改造這所大學時,許多人表示擔憂。例如,2005年,人類學部被合并入新的人類進化和社會變遷學院,人類學家為自己的學部因稀釋而不復 存在感到焦慮。但人類學家Alexandra Brewis表示,到2011年,該學院教職員的數量增加了40%,其中3/4是人類學家。其他研究位置則由應用數學家、流行病學家、政治學家和人文地理 學家占據。
混合數字
有衡量研究認為,ASU研究人員在生成學術影響方面有混合成就。就在高水平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而言,這所大學一直處于中等水平,但在過去10年中曾闖入前5名,而它通常在論文引用方面居于末位。
研究分析執(zhí)行校長George Raudenbush表示,引用率并非研究質量的最好衡量標準。他表示,出版物的相對增長是真正激動人心的,這可以看出該大學在短期內有很大進步。
另外,人們還質疑ASU實際進行了多么深刻的組織結構變化以及這些是否代表對高等教育的違背。事實上,很少傳統(tǒng)學系被淘汰;該校只是在它們之上簡單地確立了一些新部門。新學院里大部分教員實際在傳統(tǒng)學部擁有終身職位。
實際上,ASU取得的一些跨學科研究成就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傳統(tǒng)大學也設有研究中心,在這里,跨學科理念得到實施。”Jacobs說。他研究了美國25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結果發(fā)現平均每所大學有100個研究中心。
但ASU的管理者認為這里有獨一無二的東西。Crow指出,通過強調新學院和研究所,而非設立跨學科部門的中心,該校在每個不同科目間架設了渠道,以鼓勵合作。而且雇傭了思維開闊的研究人員,并將他們與技術人員進行配對,以便解決更大的議題。
作為該校正在進行的與眾不同工作的代表,Crow提到了癌癥研究的廣泛基礎。由國立癌癥研究所資助的ASU物理學和癌癥生物學融合中心,讓天體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與腫瘤學家和發(fā)育生物學家共同探索癌癥的起源和進化。
該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員已經發(fā)展出一套理論,隨著癌癥擴散,它會激活一系列對多分子生物體十分重要的古老基因。研究人員指出,深層根系和強健基因可能解釋為何一些腫瘤如此難以去除。該研究暗示腫瘤是一種組織響應,而非一系列遺傳“事故”。
Crow表示,這些出自各學科間非正常“聯姻”的成果,不太可能產生自典型的大學。“我們不想與其他研究機構問相同的問題。”
(唐鳳)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fā)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業(yè)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文章內容僅供參考。